是什么使她们走向堕落(2)
朱力亚:甜蜜爱情的苦果
不久前,朱力亚出版了自己的《艾滋女生日记》,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了一个善良女孩从幸福的天堂跌入地狱,又从死神身边重返人间的悲喜历程。
在首发式上,她说:“作为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,我希望以自己的经历警醒世人,让更多的朋友记得我的教训,学会自我保护。”
朱力亚出生在陕西一个极其普通的家庭。这个个性极强的女生,用两年时间学完了中专全部课程,并成为这所学校惟一没有毕业就被保送到大学的学生。
2003年,一次音像店中的邂逅,朱力亚结识了来自巴哈马的留学生马浪。马浪表现出的天真率直,以及那口流利的美式英语,使同样天真烂漫并苦研外语的朱力亚开始了和他的友谊。随着马浪那频繁如潮的爱情攻势,使本来矜持的女孩坠入了情网,一段异国情缘就此展开。
然而,噩梦来临得与幸福同样快捷。不久以后发生的一切,使朱力亚恍如隔世:她的爱人因艾滋病死亡,而她自己也被医院验证为病毒携带者。顷刻间,她仿佛掉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接踵而至的一系列非议、歧视,使她真正了解到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慌和厌弃,也体会到了孤独和绝望的痛苦。心理防线彻底崩溃,被学校劝退,提前毕业,更让她万念俱灰。就在她打算告别人世的时候,年迈的父母使她收住了走向死亡的脚步。在远离学校外出漂泊的路上,她问:“难道这都是我的错吗?”
是什么使她们走向堕落
晓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她其实并不担心学校和家里知道她的事,因为她觉得,如果退学了,她就可以自由地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了。她甚至反问记者:“你觉得这样的上学生涯有吸引力吗?”
朱力亚则告诉记者:“走进全新的大学生活后,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,一切都要跟着感觉走。这种盲目和自由制造了悲剧。”
“除了这些人自身的原因以外,近几年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开始侵蚀大学校园,比方说性开放等,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不好的影响。”西北某大学的学生小周说。
“高中时,我们一门心思读书,思想单纯。但是进入大学后,一下子变得很宽松,没有了高考的压力,加上没有足够的分辨能力、自我保护能力以及意志力,很多人不能自我把握,很容易迷失在都市的灯红酒绿中。”西南某大学的小高说。
陆小娅说,在从中学到大学的过渡期里,大学生很容易失去自我,放纵和沉溺不过是外在的表现,在这些行为的背后,是自我的迷失。人们有时很难理解,对于一些大学生来说,很多生活细节都可能构成压力,比如一些来自农村的学生,不会用银行卡,不会上网,甚至不会看病。加上应试教育不能回应学生全面成长的需要,使这种适应变得更加艰难。
首都师范大学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所长郭海燕认为,大学生大多处于18到25岁这样一个特殊的年龄段,太年轻,没有丰富的人生和社会经验,再加上太多的来自社会激烈竞争和学业负担方面的压力,使得他们往往心理寂寞,生理饥渴,因而用性去填补空虚,把性当作一种宣泄和消遣的方式。对他们来说,短暂的快乐,生理和精神的需求超过了对后果和责任的考虑。“这是一种对自己极其不负责的态度。”
“大学生们面对性问题应该慎重,冷静,适度,应该多考虑后果和责任,应该为自己的生命质量和后代质量考虑。在现在这样一个艾滋病高发期的环境里更应该小心,对性问题严肃对待,不要感情用事,否则会受到很大的伤害,尤其是女生,这种不慎和伤害是无法补偿的。”郭教授认为,大学里应该配备大量的心理辅导员,在性以及其他一些心理问题上对大学生们进行指导和帮助。
推荐内容
教育新鲜事
 感动你我 一个穷学生的
感动你我 一个穷学生的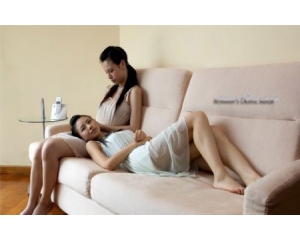 女大学生自白:我为何变
女大学生自白:我为何变